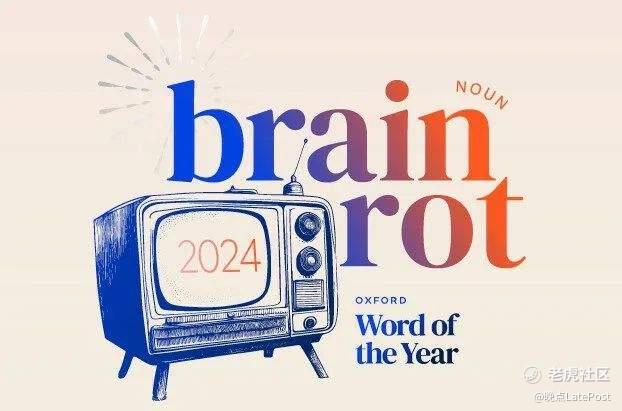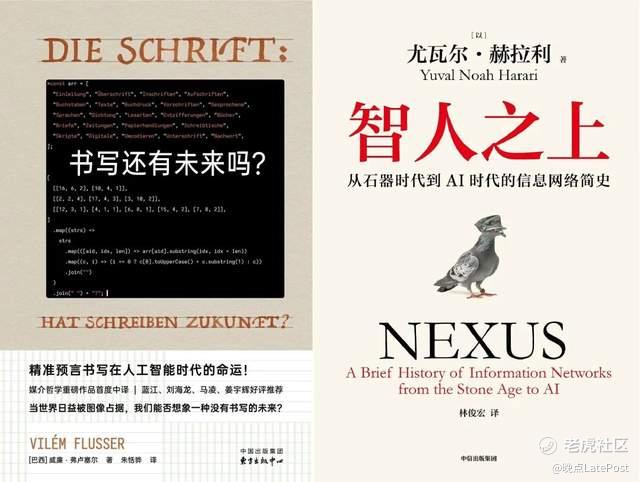“在垃圾的信息环境中,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丨晚点回望 2024 ①
和传播学学者刘海龙一起,回顾我们这一年的精神状态。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钱杨 黄俊杰
赛博朋克世界已经降临——不用脑机接口,无须在耳后插优盘。在中国,每一天,9 亿人接入微信,平均花去 1 小时 42 分钟,7 亿多人在抖音、4 亿多人在快手各刷 2 小时。还有微博、B 站、小红书等若干 “小” 平台各吸入上亿人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不等。这还没有算拼多多、淘宝、支付宝、美团等内置视频、善用游戏化设计的“工具”平台,它们的娱乐性堪比迪士尼,让人沉湎其中。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起、数万网民投票选择 “brain rot”(脑腐)作为年度词,主流网民可能倍感亲切。这个词特指过量浏览低质量信息,导致一个人精神或智力状态恶化。
网络短剧今年市场规模超过电影行业,超出科幻作家想象力的现实题材剧本被塞到数亿人眼前,成为脑腐的最新证明。但少被讨论的是,影视公司的内容创作会上早就在说 “得抖音者得天下”,现在只是再多考虑一下 “长剧短剧化”。
数字与现实被疫情和短视频加速融合。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 10 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网民(约 11 亿)每天上网时间平均为 5 小时 37 分钟,已经是 2018 年的两倍。
新的信息环境带来许多便利、重组了很多行业的分工和分配,也诞生了新的问题和争议。
前中国首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指控新首富的平台纵容网暴,把无数没话语权的人遭遇过的痛苦推到台前。施害者通常被利益驱动。一位微博用户起诉莫言 “抹黑英雄先烈”,虽然没有被法院受理,但他得到了足够的流量,开始带货、推出付费订阅服务。一些品牌也加入其中,在各类冲突中摆立场营销产品。
苏州、深圳两地的日本人学校发生遇袭事件后,许多人震惊于难以置信的谣言和情绪可以被如此广泛且隐秘地传播,只因传播者可以得到流量和相应的变现机会。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网易、腾讯、百度、凤凰、豆瓣等平台发布声明,称将打击 “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 相关违规信息。
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选择了 “brain rot”(脑腐)。图片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信息常被类比为食物。吃下去的食物影响着身体细胞的生长和变异,摄入的信息则影响着大脑的运转——一些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明,就像垃圾食品过量导致肥胖、诱发心血管疾病,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也确实会大幅改变人的大脑,造成深度思考减少,心理健康受损(如焦虑、抑郁、孤独),现实人际关系被忽视等问题。
许多人不满当前的信息环境,批判算法、平台、AI 以及流量至上的价值观,认为它们通过各种机制,想法设法让人上瘾,毁掉了人的智力、社会风气和公共生活。
这些观点都把新的媒介当成洪水猛兽。但传播学学者刘海龙认为,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哪些问题是媒介造成、哪些问题是社会造成。
“如果你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媒介,认为不使用媒介,就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过于简化了。” 他说。
刘海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他长期关注宣传、真相、信息环境、网络民族主义等传播问题,专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等。
2024 年 12 月,《晚点 LatePost》和他一起回顾了 2024 年有关信息环境的公共事件与公共话题。在近 3 个小时的访谈中,刘海龙的表达温和理性,对新的媒介环境变化持一种适应、自由和开放的态度。
“人类社会就是跟着媒介发展,人的进化也是跟着媒介变化、技术变化不断在变化。” 他不同意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技术持非常悲观和批判的态度——如技术没有叙事,导致人们虚拟化、社会被控制。
刘海龙认为,理解技术更好的方式类似达尔文的演化论。整个信息环境如同气候,人类得学会适应新的媒介形态、信息分发方式,和它一同进化。
这个信息环境将如何发展也不是一定的。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参与,哪怕你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你选择点开什么样的内容也在决定什么样的信息被制造出来,“在垃圾的信息环境里,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 刘海龙说。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刘海龙的对话。
大众文化从来都被消费主导,现在是其他选择在衰退
《晚点》:今年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是 brain rot(脑腐),澳洲麦考瑞辞典今年的年度词汇是 enshittification(垃圾化)。这两个词汇激起很多人的同感。作为传播学学者,你有什么感受?
刘海龙:我觉得好像回到上个世纪。因为在 1930 年代,收音机、电影出现时,英美知识界讨论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使得整体文化品位下降。电视时代也谈论过,像《娱乐至死》。这样的争论,每到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就容易出现。现在是社交媒体和 AI 算法分发的时代,大家又重新争论这个话题。
它反映的是媒介技术带来文化领导权力的转移。因为如果以文化质量品位划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分层的,都有精英文化、中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肯定占主导。这种转移使得我们原来熟悉的文化分层边界突然消失或者扩展了。
在中国,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只是社交媒体导致文化品位下降,更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力量对于精英文化的侵蚀。它们远远大于商业、算法。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培育起精英文化去制衡这种商业、算法导致的 “脑腐” 文化?
批评资本、算法没问题,比如不要以流量作为唯一标准,但从另一个角度,商业文化的核心就是迎合使用者。我们今天看到文化品位下降,也是使用者选择的结果。这股潮流很难阻挡,因为它是在法律范围之内迎合。大家喜欢看什么,它就会大量提供。
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社会需要其他机制补偿或者对抗这种文化,要给人上升的空间。人都会成长,从喜欢低端的文化,到慢慢厌倦,往上走。最怕的是,当人们想往上走时,没有足够多的文化供给和吸引他们。这是最大的问题。
每当媒介技术变革时,“脑腐” 文化的争论就开始出现。
《晚点》: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从来都是消费性质,关键是没有别的选择?
刘海龙:对,我们有时产生错觉,觉得现在文化很低端、世风日下。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保留到现在的几乎都是精英文化,过去的大众文化基本都消散了。而且,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较少,今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消费者。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网上职业主播数量是 1508 万。这是什么概念?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职业的新闻或者广电从业者。这相当于某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中国的短视频账号总数达 15.5 亿个,等于每个中国人有一个多短视频账号。这么大的数量,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们要填充什么内容呢?没有那么多优质内容填充,也没有那么多优质受众观看。
所以应该有其他文化对抗和平衡这股潮流。比如之前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普通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一件错误的事情出现后,有质疑、批评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小,最后都是等政府出个公告。很多事情应该媒体调查、介入,通过媒体澄清,但现在很少有媒体报道,最后就是错误、垃圾的信息满天飞、情绪高涨。但这些都不能全怪媒体。
《晚点》:一项预估数据称,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到 504.4 亿元,同比增长 34.90%。而同期内地电影全年总票房收入预计为 470 亿元,这意味着微短剧的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你看过短剧吗?如何理解它的迅速崛起?
刘海龙:我出于职业需求看了看。短剧我觉得是个替代。因为现在我们的休闲时间在碎片化,都在等待或者路上,同时工作一天非常劳累,“文化体力” 不足,使得我们没法像过去那样去电影院或者在家看剧。大块的文化消费时间蛮奢侈,这种 “加速社会” 带来短剧流行。
现在我们的文化越来越简单、微型化、碎片化。短剧跟算法息息相关,它结合了一些元素,比如前段时间流行 “银发霸总”,结合霸总和老年人。传统有起承转合、铺垫的叙事在消失,短剧变成对我们的情绪刺激。几分钟一集的剧,一分钟就要有一个爆点,让你情绪带入。所以短剧非常夸张,很多都是情绪宣泄。
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很爽,刺激多巴胺分泌。霸总剧很解气,还有被压迫后逆袭的剧。这些主题在传统影视剧里也有,但没有短剧那么极端。
它不是叙事,而是怎样操控你的情绪。很多短剧的表达,尤其对于贫富差距,都是非常极端的,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但它利用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缺陷。
作为纯商业产品,短剧可以存在。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有没有好东西跟它对抗?如果所有都是这样,那就完蛋了。
《晚点》:很多人也想看好东西,但没时间,平常生活太辛苦了。
刘海龙:对,可能一些短剧也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像外卖员等外卖时可以刷短剧或者短视频,否则他每天就只剩送外卖。之前网上有人讨论 “电子阳萎”,连打电子游戏都提不起精神,问题显然出在生活环境中。
AI 生产海量信息,正在让我们丧失时间感
《晚点》:相比之前的媒介技术变革,今天因为算法、AI 等技术的出现,虚假信息猛增。像今年韩国深度伪造色情犯罪激增,中国一些账户利用 AI 生成虚拟人卖货,你怎么看?
刘海龙:最近 Sora 发布新版本,又引来一波关注。类似这样的新技术,使得 AI 生成的信息会越来越像人类创造的信息。
现在有人观察到,我们搜索,AI 生成答案,但生成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会根据算法,越来越靠前。未来我们搜索的内容可能是 AI 生产的东西占主导,这些东西又成为新的语料喂给 AI,然后 AI 又会加工 AI 生产的东西,不断反复。这就会出现 “递归效应”,出现尼采讲的 “永恒循环”。
信息的永恒循环会产生一些危险。比如我们会失去时间感、历史感。最新和古老的信息都是突然一并涌入,不像书籍那样的线性时间排列或者秩序。现在接受社交媒体和推送内容这一代,其实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活在当下,不太关心历史,忘掉了历史教训,导致觉得当下最好、一切合理。
像吴柳芳事件,我看到有人说,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历史上靠擦边擦出来的。比如电影里的吻戏、杂志上的泳装照、李谷一的 “气声唱法”,当年都是冒着被查禁或者批评的危险。一点点地,通过类似这些事情,人们的道德尺度开始放开,社会变得更加宽容。如果没有历史意识,就意识不到封禁一个账号意味着什么。
还有因果性的丧失。人们搞不清楚很多东西的因果关系。像今天许多人都是以我的情绪为主,被情绪裹挟,不会推理一件事情合不合理、正不正确。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因果、反历史的。
AI 如何影响人类的信息环境还是个未知数。
《晚点》:你觉得如何能降低负面影响?
刘海龙:因为 AI 不能自己识别自己。现在最强的技术都是 “生成”。“判别” 意味着水平要比 “生成” 高。同时,今天 AI 生成的内容大部分基于文本,没办法和现实对照。很多荒唐的内容,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现实感或者历史感。
那怎么让 AI 有现实感?我觉得技术的问题可能还得技术来解决。因为人类识别不了那么多信息,不可能一条条核对。AI 未来可能要往如何感知现实、识别现实方向发展。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这种 AI 开发,如何识别或者筛选虚假信息,这样未来可能好一点。否则,这轮技术发展可能会是灾难,大家以后都无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晚点》:虽然 AI 生成了很多低质量、不真实和不准确的信息,但你在《生产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一文中提到,AI 生成的知识也具有创造性。
刘海龙:我的主要观点是说,AI 生产的知识跟人生产的知识不一样,不能用人类的知识标准要求它。这里面涉及很多哲学讨论,比如 AI 生产的知识能否自我解释,能否指向现实,有无创造性,背后是否有情感等等。这些讨论我就略过。
现在 AI 生产的知识,人类的参与很深:一是语料来自于人;二是问题来自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创造的哲学是由苏格拉底的问题引导出来的,所以人的问题引导对 AI 的知识生产很重要。
另外,我们过去认为机器没有创造性,但 “创造性” 是人类产物,意思是打破人的预期和规则,并且要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内。比如梵高打破常规画画,但人们理解不了,生前卖不出画。后人将他的创造性解读出来后,我们才认为他有创造性。所以创造性是人类的标准。
那现在看 AI 是否有创造性,主要看的也是人类标准。因为对于 AI,生成的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根据统计学计算出来。对 AI 的评价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这就像佛教讲的,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的心动。
还有,现在的 AI 依赖于人类数据,但下一步可能发展到不依赖人类数据,就是只有算法,没有数据的 AI。AI 能自己获得数据。这时,AI 生产的知识会达到新的高度。
比如最早 AlphaGo 是用人类棋谱,到后面 AlphaGo zero 完全没有人类棋谱,自己从头到尾通过自我对弈,总结想法,更厉害了。这也有点像李飞飞他们讲的空间智能。AI 能感受这个世界,建立起时空秩序,能够不依赖于人感知和推理。
《晚点》:到那个阶段后,人类的知识生产会受什么影响?
刘海龙:到那个阶段,可以说 AI 具有意识。人类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小,或者很多东西 AI 会给我们参照。人类的知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这就涉及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讲的,不同政权怎么认识这类知识,用还是不用,会出现很大争议。
平台内容治理,更多让言论市场自己解决
《晚点》:你怎么看待钟睒睒陷入的舆论风暴和他对平台和算法的批评?平台的内容治理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你觉得企业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什么?
刘海龙:我觉得平台的内容治理不能仅靠政府,需要平台、法律、民间组织、普通公民等一起参与。政府要考虑到权力边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治理,不是 “一禁了之”。
在中国,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平台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借着治理旗号进一步管控,缩小普通人表达的权利。比如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的视频,只要不违法,是可以存在的,没必要把边界拉得那么高。不然会造成普通人表达空间越来越小,对整个社会不利。
社会需要一些表达出口,哪怕是情绪发泄。如果对这些表达堵得越来越多,可能造成高压锅缺乏泄气阀,越来越危险。
我问过一些平台,它们也有治理政策,比如当一个内容点击量过高时,会触发人工审核机制,判断这些内容适不适合传播。像钟睒睒说到的诽谤和虚假信息,平台可以处理,调整算法,包括降低权重,减少扩散,做些标注、提醒用户等。
但我觉得更多要交给言论市场自己解决。平台本身有某种自我净化机制。关键在于,你要让不同意见能在里面表达。不是所有问题都要政府介入,政府也不可能管理每件事情。要有常态机制,像吴柳芳这样的视频,线定在哪里?我觉得整体还是宜松不宜紧。
《晚点》:具体到钟睒睒提出的问题呢?
刘海龙:钟睒睒做过传统媒体,我觉得他在用传统媒体的思维讨论短视频平台。因为短视频平台不是一个大家看到内容完全一样的地方。每个人看到的内容,跟他自己的偏好、之前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比如钟睒睒和钟睒睒周边的人,肯定大量观看农夫山泉的内容。因为他们会搜索、关注,很自然,在他们眼里,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或者虚假信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
传播学有个概念叫 “第三人效果”,就是你认为这个信息的内容对别人的影响很大。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算法、AI 成为新一轮媒介技术变革争议的焦点。
《晚点》:不过钟睒睒的事情还是一个网络热点。
刘海龙:那为什么这样的内容点击率高?大家在电视时代也讨论过。有个理论叫 “培养分析”,说商业化体制会使得某些内容高度同质化,比如暴力、丑闻、名人,它们就是会受青睐、收视率高。从长远来看,它们维护了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
今天也是一样,有些内容就是点击率高,比如仇富、民族主义。商业迎合受众,但这种迎合也是受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名人因为社会责任和回报比较大,相对来讲,个人权利要小一些。不能说到你,就被认为是诽谤,还有许多是正常的讨论和舆论监督,以及灰色地带。有时,平台也不能判断谣言、诽谤,有些可能过两天就变成真相了。
任何人都不掌握绝对真理,为了大家有更多表达自由,要留出一些空间,容忍一些 “错误” 信息传播,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钟睒睒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处理,但不能什么都 “政府站出来主持公平”。这不是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
《晚点》:你曾研究过 “帝吧出征” 为代表的网络民族主义,如果回看它在 2024 年的变化,似乎趋势是极端化、商业化、回旋镖效应(反噬)。你觉得这些年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什么变化和新特点?
刘海龙:我们讨论 “帝吧出征” 时,基本上还是人在行动,通过网络动员参与。现在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者加上了技术,尤其是算法。极端内容有争议,评论转发就多,点击率就高。热烈的数据使得这些内容被平台认为很有价值,然后在算法的作用下,就会越炒越热。
现在的网络治理,对网络动员和网络行动的限制非常大。一方面,这打击或者压制了饭圈等不良行为,但另一方面,过去比较正面的集体行动也在变少,导致现在没有力量去制衡另一面的言论。没有制衡后,它们就无限膨胀。比如胡锡进过去被列为左派,现在他被某些极端派看成了右派。当真正的右派没有时,中间派甚至左派中的温和派都成了右派,整个政治光谱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
网上关于农夫山泉的言论,说 “茶” 字像日本的靖国神社,红色瓶盖象征日本国旗,千岛湖说成富士山……这很荒谬,但有流量。
这些信息需要被反制。但我们现在只剩国家介入,强制平台做些事情。这样,总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红、喷子、骗子、瘾君子……社交媒体世界似乎越来越虚假和极化。
《晚点》:网络上很多事情都会呈现撕裂和极化的特征,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一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作者克里斯·贝尔通过实验证明,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打破 “信息茧房”,接触对立观点,人们仍会产生政治立场极化。
这个研究很有启发。但你也说,贝尔没有考虑政治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网民在遭遇不同意见时,并不一定会出于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走向极化,更多的则会观望现实政治环境和网络意见气候后再谨慎行动。能不能再讲讲你的比较、观察和思考?
(注:贝尔称,社交媒体是一面会扭曲用户对自我和他人认知的棱镜。社交网络用户遭遇不同观点时,会强化原来的身份认同,为了捍卫立场变得更加极端。温和派在看到极端言论后,认为社会分歧太大,感受到巨大压力。温和派越沉默,极端声音就越放肆。这种扭曲会让用户形成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虚假政治极化,从而变得越来越极端。)
刘海龙:这本书的作者讲,网络有两个作用,感知环境、表达意见。在大众媒体时代,人们感知的是大众媒体环境,表达意见是私下表达。两者分开,使得个人表达没那么大影响力,可见度比较低,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会造成少数极端言论非常显眼。它点击率高,加上算法推荐,导致人们觉得这样一些极端言论好像代表了一个社会真正的声音。
但极化本身需要条件,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声音表达。我们现在的声音表达不平衡,很多人看到大多数人赞成某个观点,或者某些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他们就不敢表达。比如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可以表达,但批评他们的言论,表达起来就多有忌惮。这会导致我们出现一种结构性压力,使得整个政治光谱发生巨大变化,言论越来越极端,大家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的舆论场经常表现出来的是 “虚假的政治极化”。
《晚点》:与极端言论相关的还有网络暴力。这些年,韩国、中国等地网络暴力造成的悲剧频发。你觉得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改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网暴,尤其现在你还不能确定骂你的是真人还是水军、AI。今年有一则法律判例,3 名网暴者被判在微博上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但运用法律解决的是少数。
刘海龙:“网暴” 这个概念,现在大家使用得比较随意。网暴有不同类型,比如有的就是单纯网络攻击或者批评;有的批评只有两三个人参与,但有人觉得是网暴;还有的是 “开盒”,在网络上公布你的真实地址,让人到现实中骚扰你。网暴也和承受能力相关。比如很多人骂胡锡进,但他不觉得自己被网暴,而钟睒睒可能就觉得压力就比较大。
董天策教授做过一项研究,分类整理了学术论文中提到过的 55 起 “网暴” 案例。他发现,有司法介入的 “网暴” 只占到 27.27%;在无司法介入的 “网暴” 中,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占到 47.23%,网络谣传、网络事件、网络攻击占到 25.4%。他认为,现有案例对 “网暴” 的认定扩大化,既不符合司法实际,也非规范判断,实属臆断。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过《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那份文件提到,针对网络暴力的不同行为方式,要准确适用法律,以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定罪处罚。我觉得网暴还是要按照法律的方式界定比较好,因为扩大化会影响正常的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
《晚点》:有时候人们也会夸大网络舆论的影响。
刘海龙:对,这涉及受害者能不能回避?比如仅限于网上攻击,那我可以不上网,“熔断” 一下,逃避影响。网络相对来讲是可以逃避的。
有时你被骂,也要反思自己的问题。比如有人在性别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那人家骂你,这个时候首先要反思的是,谁让你说这话?没有网络之前,也存在这种 “舆论审判”。
作为普通人,我们要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我们也不能把网络世界作为生活的唯一世界,好像那个世界没有,就崩塌了。比如四川德阳女医生因网暴自杀事件,这是场悲剧,但也可以避免。
过去也有反智主义,但大家看不到
《晚点》:今年数学家丘成桐在演讲中称中国现今数学水平没达到美国 1940 年代,然后被骂 “汉奸”“公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像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叫《专家之死》,就把这种现象和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思潮关联在一起了。
刘海龙:就像奥尔特加·加塞特讲的,这是一个大众反叛的时代。当大众突然有了发言权,过去精英没办法听到的声音就表达出来了。过去也有反智,但大家看不到、听不到,就认为不存在。其实现实世界一直是这样,只是现在可见度更高。
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怕的地方是反智加上民粹,不信任整个体制。人们不是不信任某个专家,而是不信任既有的科学、理性、法律的体制,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耐心。那当一切都不可信时,你根据什么判断和行动?
《专家之死》里也提到,过去我们认为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智,但在新一波的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里,反智的人的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他们也开始不信任整个制度。这跟整个全球的互联网化有关。我们看了太多负面,让我们以偏概全,不恰当推广。
因此不仅普通人,公务员、决策者的科学素养或者批判性思维,都要提高。
还有我们的真相寻求机制。因为传统的真相寻求机制有三根非常重要的支柱——新闻媒体、法律、政府调查。如果三方协作,我们能获得真相。而且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相互监督,然后相互完成真相的获得。如果三支力量不平衡,我们无法验证真相,只能单纯质疑,那就会产生许多阴谋论、反智主义、垃圾信息等。
大众在反叛,专家在消失。
《晚点》:如果反智主义的趋势延续下去,你觉得后果可能会是什么?
刘海龙:当没有外在标准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时,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权力大,谁就左右舆论场。最典型的是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科学标准被推翻之后,就是政治的标准。这是最可怕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典型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看上去好像每个普通人在发言,但其实不是的。
《晚点》:大众文化呢?
刘海龙:大众文化或者商业文化可能会产生垄断,但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因为消费者是多变的,不会永远接受某类东西。私有财产也需要民主和法治来保护自己,要依靠理性的逻辑来维护自己利益。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不可能只有商业文化。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