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伊诺在演出现场,摄影:Pete Woodhead
张璐诗:这位创作涉猎颇为广泛的音乐艺术家,曾希望寻找一种语言,能够全面概括形容文学、绘画、建筑、音乐等文艺形式。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璐诗 Lucy Cheung
75岁的英国音乐艺术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上周末登台伦敦南岸中心的皇家节日大厅(Royal Festival Hall),与爱沙尼亚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Kristjan Järvi)率领的波罗的海爱乐(Baltic Sea Philharmonic)一同,举办了他有史以来在英国的首场个人音乐会。而且一晚连续演了两场。
作为“艺术摇滚”的先驱、“氛围音乐”的创始者、以及极简风格电子音乐在英国的先锋,布莱恩到了今天才首度举办个人音乐会,似乎有点难以想像。但事实上,布莱恩是音乐界一位独特的人物,或者说,他大半生都在饰演“斜杠青年”,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而闻名。比如在意大利,他首先是一位声音装置艺术家,在德国,布莱恩则以他跨领域的演说著称。他长期关注和活跃的远超文艺领域,比如2019年在STARMUS科学双年展上,他因科学传播上的贡献而获颁“史蒂芬•霍金奖章”。
虽然当代英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处处可见布莱恩的影响,但作为音乐人,无论在早期的摇滚组合“Roxy Music”,与大卫•鲍伊的长期合作,还是后来与U2、Coldplay乐队的合作,布莱恩一向担当的是键盘手或制作人角色。个人音乐会姗姗来迟也有道理可循。在布莱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之中,他的个人作品有不少是自己担当人声的。这个晚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部分作品。
与他携手合作的克里斯蒂安,来自爱沙尼亚著名的古典音乐世家:他父亲尼姆•雅尔维与兄长帕沃•雅尔维均是活跃世界舞台的指挥家,同样作为指挥家的克里斯蒂安,则为自己构建了一条偏向当代音乐和灵活舞台设计的道路。这次他带到伦敦的“波罗的海爱乐”,就是他创建的乐团。这个乐团明年3月还将带上波罗的海的重金属音乐作品参演香港艺术节。
布莱恩与克里斯蒂安的合作,来自威尼斯双年展委约而实现。身兼作曲家的克里斯蒂安,将布莱恩的氛围音乐和极简电子音乐作品逐一编配成管弦乐编制。现场听感,他的改编细节与层次都丰富迷人,毫无许多改编管弦乐作品的气势有余,内容乏味。经过各种真实乐器的解构演绎,人们甚至得以对“氛围音乐”的原创性获得了进一步理解。
布莱恩•伊诺的演出现场,摄影:Pete Woodhead
回忆布莱恩•伊诺在北京
差不多20年前,布莱恩曾到北京的日坛公园创作了一场声音装置。他在公园拜台的墙内四周安装上英国和中国风格混合的“钟圈”,参观者看不到太多动静,布莱恩希望大家能有“就像坐在河边”的感受。这个装置呈现的依然是“氛围音乐”的理念,布莱恩同时也结合了自己早年学绘画的经验:他创造的是声音的图景,要让宁静更宁静。
回想起来,今天古典乐界倡导的“让音乐脱离传统的音乐厅”,在布莱恩的世界中很早已经发生。当时布莱恩在公园里安装“钟圈”时,在一旁放风筝的老头走过来很认真地说:“我对你的音乐很感兴趣”。后来我与他在日坛约茶聊天。期间我问起他对声音装置与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想的,布莱恩回答说,他早年学了好几年的美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录音技术刚开始普及时,他又花了好几年去研究怎么用录音带做录音:“慢慢地我就觉得,录音其实挺像绘画。录音的过程,就像在一种颜色上加上一种颜色,组成另一个画面。当我觉得绘画比音乐有趣的时候,就想做出‘声音的图像’”。
由此,到了1970年代,布莱恩全部的创作都是在用声音“画画”,并且逐渐将人声减掉。那就是“氛围音乐”的雏形。布莱恩形容:“没有开始,没有过程,没有结尾,也没有故事,只提供一种状态。就像我在日坛公园的装置,是要让大家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空间,可以放松,什么都不做,同时旁边没有干扰。”
布莱恩在北京时,特别喜欢看日坛公园里老头老太太的活动,他说感觉这样的活动很开放。但当他选择了公园作为创作艺术的场所,布莱恩的原则是“艺术家没有权利骚扰到他人”。他认为像公园这样的地方,人们是来寻求安静的,在这里创作,好处是有空间感,而作品应该是增添这种氛围,而不是破坏:“很多时候我做音乐,只是设计一个系统,解决了技术问题,就任其发展,音乐自然而然发生的时候,我不是乐手,而是听众。”
这时我想到了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布莱恩接过话茬,他说凯奇是想让生活与艺术有重叠的轨迹,而他则相反:“我想将我的生活与艺术分开,我要参与艺术,只因为艺术跟我的常规生活完全不同。艺术也跟宣传无关,宣传是你套上了艺术的外装,像商人一样兜售你的创造。而且约翰•凯奇创造了一个系统后,无论如何就那样了,但我创造了一个系统,不满意了会拿掉,重新创作。”布莱恩认为,作为实验音乐家,必须承认有时候自己是失败的。
早在三十年前布莱恩就注意到,大众通常只盯着眼前的事情,比如政府机构大多做的是五年、十年的计划;公司只写年度、季度报告。1996年,布莱恩与一批科学家、哲学家和“未来主义者”创建起名为“马上着眼长远未来”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他们的愿景是面向未来一万年,去创造出启发大众思考长远未来的项目。布莱恩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英国一所建于15世纪的大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发现天花板上的木梁岌岌可危,于是就向园林署人士提出要换房梁,园林署回复说:“我们一直就等着这一天,园林里的树都是为此准备的。”布莱恩说,这就是“马上着眼长远未来”制订项目的方向。
布莱恩说,自己一向对世界的构成、事物的状态、进化论这样的话题十分好奇,他想知道事物以前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科学帮我解决这方面问题。我不信上帝,所以我会从别的渠道想问题。我做的很多音乐,都是把很多简单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交错,发生反应,从而产生错综复杂的新事物。”
这时我想到的是:科学与艺术都无非是看世界的方式。但布莱恩说:“吸引我的倒是这两者不同的地方。科学偏机械性,做试验,然后用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告诉大家结果如何,应用到生活中。而艺术,你捉摸不透到底原理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触动了你。对艺术,你会表现一种屈服。而科学,刚相反,是一种控制。”
布莱恩•伊诺在演出现场,摄影:Pete Woodhead
布莱恩曾希望找到一种语言,能够全面概括形容文学、绘画、建筑、音乐等各种文艺形式。他说,历史学家经常就艺术的定义提问,而答案一般是交响乐、美术、手工艺等。但他认为,舞蹈、时尚潮流等当代存在的一切,都在艺术的范围内:“文化,跟风格有关,于是文化就是在我们生存所需之外的风格。”他从几十年前开始就经常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纯白的盘子上画图案?为什么要把盘子的四周磨成这样复杂的形状?人类考虑实用还不够,而是一向、反复地在雕琢风格,为什么?
我问他找到答案了吗?布莱恩说自己想了很久:“我们总是在装饰自己、在乎外表怎么样,所以我说,所有的人类都在创造艺术。同时我发现,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天赋,是擅于想像,而且会创造出‘想像链’,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很多人一起思考,一起做事。人与人交流,需要对对方的思维有个起码的印象,我们称之为‘思维理论’。比如读一部小说,你要先进入作者的世界,然后再进入作者设计的种种角色的思维。我们需要不断‘排练’我们的思维,于是需要不断锻炼进入别的想像世界,比如我看着这个盘子,会想像两三千年前的中国人用也是这样的盘子。艺术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的思维‘排练’。”
布莱恩说,他在文艺界的朋友,没有一个能跟他聊这些话题:“科学家通常需要都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但艺术家刚好相反,他们的语言都是与世隔绝的。这方面尤其体现在流行文化上面: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刚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一位记者见到我以后顿时一脸失望――他以为,摇滚歌星都该是半颓废、半疯狂的样子。我曾被媒体形容为‘没感情的家伙’。他们认为冷漠同时又狂热的那样子才算有性格,”布莱恩继续说:“回头再来看看今天的许多艺术家,他们在作品中常常故弄玄虚,让外界感觉自己在这个领域很重要。诸如此类,我觉得当今艺术界的氛围太可怕了。”
布莱恩•伊诺曾在电邮中向我推荐两本书:
1998年出第一版的詹姆斯•C.司各特写的《像国家那样看世界》(“Seeing Like A State”),副题是《改善人类困境的一系列计划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挺简单: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最想达到的是,他们操纵下的现实可以很“清楚”。“清楚”一词是作者一再重复使用的,在书里的意思是“遵循简单、明确的命令”。书中一半内容都在描述人们如何尝试改善人类条件,另一半则说明到底这些计划是怎么样和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还讨论了以下几个话题:令城市及城市中的生活、语言易于跟从;作为“清晰性”演习的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义务村有化;农业的工业化(“征服自然”),并逐个对现代化的实验和现代化之前“不清晰”的处理事情方式做对比。这样,巴西利亚就是个清晰、井井有条的城市,可是要让城市发展起来,巴西利亚周遭又不得不围绕着“不清晰”的棚屋,以便发挥城市的主要职能。这样的例子在书里俯首可拾,都很相似:要改善一处的状况,必须把原有的复杂和混乱清掉,然而被淘汰的复杂性又不得不走旁门侧道再次被引入,以维持大局有序不乱。
由此及彼,另一本书是斯图瓦特•布兰德写的《高楼如何学习》(“How Buildings Learn”),这本书是关于建筑及其成败之处的。书的内容很丰富,而且会使还留有社会工程主张的人倍感困惑,并不是说这本书反对社会工程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得按着先于这个时代的解决方案走,即使方案杂乱难懂。”这是对复杂、先锋的系统一次智性的研究——也可以测试让一条不紊的思维去理解这些有多难。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这是20世纪的一个从乌托邦到地狱的故事,“现代主义者”欲认同人类与社会当中先行的智性,但最终失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
商业财经 国际视角
关注FT中文网视频号
往期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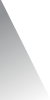
喜剧缓和糗事人生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