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很多人把时代的赠予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未来要考验硬功夫。”
文丨高洪浩
编辑丨宋玮 钱杨
“回想这项投资,我有诸多感慨和遗憾。”
“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
从事 PE(私募股权)投资 30 年,孙强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失败,这在一个赤裸裸以挣了多少钱论成败的行业不多见。
10 多年前,孙强开始动笔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投资经历记录下来,最近以《一个投资家的成败自述》为题出版。他不愿意强调个人,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写进标题,而是以自我检视的口吻回顾他主导和参与过的 PE 投资项目,剖析从失败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张磊、沈南鹏等同行的故事比我有意思一百倍,我没他们那么成功,所以敢写失败”。孙强笑着说。
7 月上旬,孙强在广州有两场新书分享会,他没有助理和专车,独自一个人背着双肩包穿梭在两个会场。他年过六旬,但因为天天练太极、健身,看起来精力充沛。他讲话语气谦逊、声音极轻,像个学者,没有所谓行业大佬通常显示的强烈的目的性、咄咄逼人的感觉。
1995 年,孙强加入沃伯克·平克斯(E.M.Warburg Pincus & Co.),成为这家老牌美国私募公司的第一名华人雇员。他从这两个犹太姓氏里各取一个音,为公司起了 “华平” 这个中文名字。
作为中国最早进入 PE 行业的从业者之一,孙强完整参与了 PE 在中国从无到有、从草莽到成熟的全过程,逐渐执掌华平亚洲区的业务,后来加入 TPG(德太投资),任中国区主管合伙人和董事长,先后主导和参与投资项目近百亿美元,支持了 7 天酒店、国美电器、红星美凯龙、汇源果汁、乐普医疗、和睦家、绿城中国、银泰百货、神州租车、58 同城、APM 摩纳哥、度小满等企业的成长。
进入中国以来,华平一直是这里最活跃的外资 PE 之一——对多个行业的超过 170 家企业累计投资超过 160 亿美元。相比之下,KKR 在中国投资企业数量只有 40 余家,累计投资额在 70 亿美元左右;凯雷的累计投资额则在 100 亿美元上下。
孙强给人一种见过风浪、平静通透的印象。他似乎不那么在意错过某个热门项目,而是认为只要投准少数优秀项目,保证基金回报即可;就算是抢项目,他也在意 “体面”,在意 “吃相”,对于一些人的做法直言 “我做不出来”、“这违反了我的原则”。他喜欢说 “和气生财”,为了避免冲突,曾出让原本已经拿到的份额;他还因与企业创始人结下深厚情谊,延误了项目退出的最佳时机。这让孙强身上多了一些 “人性” 的味道,也让人为他遗憾 “没做出更大的成绩”。
孙强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谈论 “失败” 而不是 “成功”,他知道成功的原因可以很模糊,而失败于什么可以很清晰、有意义。
在过去二三十年机会遍地的时代,一个人犯了点错,下一次还能挣到钱。但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投资路径已经中断——募投管退的难度在增加、好的项目更少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孙强讲述的 “遗憾”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
“看时机、看赛道、看团队,这就是决定投资成败最关键的因素。” 孙强总结说。
最早的 PE 投资人,在不成熟的市场摸石头过河
1992 年底,在高盛任职的孙强从纽约搬往中国香港。当时,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如火如荼,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推动了一批即将赴港上市的企业,外资投行们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蛋糕。
然而孙强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投行的工作。“这是份要求人的活,不仅业务得过硬,还要能 ‘甩开马蹄袖下跪’,恳请客户认可。” 孙强在书中写道。两年后,他从投行部转岗到了直接投资部(PIA)。投行投资部看中的一般是中后期相对成熟的企业,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 PE 这个概念。
直到 1994 年,高盛直投部在中国只试水般地投资了广西玉柴动力、北京东方广场、平安保险和上海的一座冰淇淋厂,其中平安保险的投资额最大,但也仅 2500 万美元。
那时,中国大型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营企业,它们不太欢迎单纯的财务投资,更愿意与有产业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合作。孙强走访过上海的大白兔奶糖、三枪集团、梅龙镇集团,甚至是杭州的萧山机场集团、张小泉剪刀,处处碰壁。
直到 1993 年情况才开始转变。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高速发展的民营企业,但由于缺乏能够承受风险的股本投资,这个群体面临着相同的融资难题。
敏锐及熟悉中文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人最先看到机会,于是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凯德(CapitalLand)、Crimson、Walden、H&Q、PAMA 等机构冲了进来,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大鳄。
1995 年,孙强离开高盛加入了美国老牌私募基金华平,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一位华人员工。华平成立于 1966 年,曾投资过知名的企业级软件服务商 BEA Systems、电信公司朗讯、芭比娃娃制造商 Mattel,以及梅隆银行 Mellon Bank。
1996 年,在投资银行罗伯逊·斯蒂芬斯(Robertson Stephens)任职的冯波找到孙强,希望他能投资一家从事互联网系统集成业务的公司。这家公司叫亚信,是旅美中国留学生田溯宁和丁健所创建。亚信与美国 Sprint 公司联手,协助中国电信在北京、上海安装了两个互联网测试节点后名声大噪,合作邀约纷至沓来。
投资双方都有合作意愿,最大的矛盾在于如何估值。亚信预测明年利润将达 900 万美元,根据 10 倍市盈率,得出 9000 万元的估值。他们认为按照亚信的成长速度,这个估值并不高。但孙强将信将疑:“900 万美元的利润,他们真的能达到吗?” 他仔细查询后发现,亚信的预测并没有任何财务模型来支撑。
双方商定,由华平从总部调人来帮助制作财务模型和做尽职调查。数周后,华平团队得出结论,亚信未来的年平均利润至多达到 200 到 300 万美元。据此,华平提出按 3000 万美元投前估值投资。
在一家会所的单间里,几位创始人努力说服孙强接受他们乐观的预测。“中国互联网的前景无限,而亚信只需要把电信部门的规划变成现实,就能实现财务目标。” 然而孙强还是没被说服:“作为投资者,我们的估值一定要有数据支撑,才算合理”。
谈判胶着之际,孙强提出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如果亚信真能达到 900 万利润,华平就认可 9000 万的估值;完不成,利润应与估值挂钩,固定市盈率乘以实际完成的利润,就是双方认可的估值。争执到凌晨,双方才达成共识。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 “对赌”、如今已成私募投资的常用条款。
“对赌” 在中国的投资交易中出现频繁,而在创投活跃的美国硅谷却不常见。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一旦产生利润,可能与去年截然不同,无法按传统年度利润估值;二是创始人对企业未来的前景过于乐观,投资人无法说服他们相对保守,只能让他们对自己的预测负责;三是中国商业社会发展尚未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有效遏制及惩罚造假的制度,投资方只好依靠合约对赌来制约对方,甚至后来还发明出了以不造假为条件的对赌,比如九鼎投资当年与宜都天峡的对赌协议约定:如果企业没有造假,那么将予以创始人奖励,反之则需要补偿投资方。
除了估值,PE 投资更大的挑战是在投资后提升价值、退出的过程。
在美国有大量创业者通过并购卖掉公司,但很少中国创业者愿意这么做。“多数人认为被并购,或是被控股是一件丢脸的事。” 一位中国本土的投资银行创始人说。即便实现了收购,找到能接手改造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不容易。PE 退出的另一个障碍是中国证监会对内地企业的大股东减持有诸多限制。
在当时的中国,机会看似很多似乎很多,但在不成熟的市场投资不成熟的企业,有无数挑战,很多事情得摸着石头过河。
建立行业团队精准投资
千禧年前后,全球掀起互联网投资潮,华平也没能坐住。孙强和同事祖文萃、郑可玄、程章伦、冷雪松一口气投下了十余家早期互联网公司,包括 Go2Map、8848、亚商在线、浙大网络、港湾网络等。
在电子商务明星企业 8848 这个项目上,孙强找到了 8848 的股东、IDG 资本创始人熊晓鸽请求帮忙。对方同意预留 100 万美元的份额,但要求华平三日之内签约汇款,不给做尽调、不能谈判条款。
按照华平内部流程,投资企业必须进行法律、财务、经营、市场等方面的尽职调查,而且要求签署必要的股东权利保护条款。然而在所有人都被狂热的互联网浪潮冲昏头脑的时候,“竟然鬼使神差地拿到了公司的批准。” 孙强说。
惨痛的失败接踵而至。2000 年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华平的项目中,8848、 ABest 与 Nissi Media 的投资直接清零,其余的项目,表现最好的能收回成本。
这是孙强进入 PE 行业后的一次大挫败。痛定思痛,孙强和同事们都认识到,做 PE 应该正本清源,不能追赶热潮,而是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行业,发掘企业的核心价值以及合理的资产价格。
团队讨论后认为,华平的资金体量和投资偏好使它更适合专注 C 轮以后的项目,以便规避产品、市场和团队的生存风险,提高项目的成功率。“需要钱来拓展的企业才是最值得投资的。” 孙强说。
这样的投资框架,就排除了未经验证的全新商业模式和看似潜力巨大、但要烧巨资若干年后才有机会一飞冲天的早期企业。
2005 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加速,中小板的出现使大量民营企业得以上市融资;股权分置改革后,过去不可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也得以进入市场交易,投资退出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中国经济的腾飞、资本市场的垂青,让全球顶级 PE 在中国全面扩张,鼎晖、弘毅等本土私募也茁壮成长,甚至国营机构也涌入 PE、VC 行业。
在华平中国,孙强和团队正讨论着未来的投资方向。他们判断:2000 年以后,中国将迎来城镇化浪潮、中产阶级涌现、基础建设大升级、制造业崛起、人口老龄化等变化。根据对于这些大趋势的分析,孙强决定聚焦在零售消费、房地产、医疗健康、科技与媒体四个行业。
孙强在华平中国的一个举动,是建立垂直的行业团队,让他们深入研究细分领域,便于和创始人沟通,并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这是在当时的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里率先迈出的一步,包括建立专业的地产投资团队。
PE 投资地产并不算新鲜事,但美国地产基金通常投的是单个项目和固定资产,比如一栋写字楼或者一座商场。而在中国,地产开发具有规模效应和快速周转、高速增长的特点,华平把住宅地产看作类似快速消费品的增长型投资,用行业视角、公司视角来投资地产,获利于规模和品牌效应。
中国的地产商不同于美国的同行,在那个大基建的年代,无论住宅或商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因此中国的地产商都是滚动式开发项目,甚至同时开发若干个项目,这使得他们对资金有大量的需求,公司体量、收入也会因此不断增长。
“当时国内的很多投资者没有意识到地产公司本身也有品牌价值。” 孙强说。2005 年起,华平先后投资了富力地产、华润、阳光 100 等住宅地产企业,以及红星美凯龙、银泰百货等商业地产企业。
2005 年后,华平在中国的业务和团队规模也不断扩大,投资团队发展到 40 多人,成为了中国最活跃的外资 PE。
成熟的商业社会才有 PE 更多的机会
多数人只看到了大交易表面闪耀的投资数量和金额,但这往往是起点,成功退出才算完成了一桩好交易。这其中,“创始人” 和 “团队” 是影响投资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5 年,华平携手法国食品企业达能投资了汇源果汁。当时,汇源在中国纯果汁市场占有率达 40%,但在管理与营销上存在明显短板。于是,华平与达能专门帮它制定了改善运营的 “百日计划”,达能直接派了六名高管入驻,辅助汇源管理市场、渠道和运营等部门。不过计划最后没能推下去,达能派来的总经理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汇源的 “首席模特”,意思是没有实际管理权力。
两年后汇源的利润创新高,达到了 2.77 亿港元,较前一年翻了 2.5 倍。但股东担心,这个成绩是汇源为了完成投资时的对赌而做的财务操作——将利润提前在 2007 年提现。
董事会上,孙强与达能管理层一起,要求汇源不要再盲目扩大产能,而是重视市场开拓与铺设渠道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当即驳斥,“你们懂管理吗?我天天扑在一线,你们不了解情况,就不要指手画脚!”
后来的结果验证了孙强的忧虑。刚进入 2008 年,汇源税后利润急速下降,跌幅超 70%。下一年,汇源出售给可口可乐的计划因中国商务部的禁令而搁浅,公司股价从 10 港元急挫至 3.99 港元。眼见回升无望,孙强决定将华平持有股份出售给荷兰银行。华平退出后,汇源的业绩一路下滑,债务不断上升。2017 年,这家公司的负债率已超百亿。四年后,汇源破产。
这个项目表明了投资后企业的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管理不善,投资者又不能对创始人形成有效牵制、对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偏,投资时看似优秀的企业也会出问题。
在中国,因管理层更迭陷入混乱、管理层与股东理念相悖引发冲突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2016 年,中国餐饮品牌大娘水饺的创始人吴国强发出了一纸公开信,控诉股东、老牌欧洲 PE 巨头 CVC 对企业的改造。后者在控股后的三年内汰换了三任 CEO ,但大娘水饺的经营仍每况愈下。2014 年,CVC 还获得了俏江南的控股权,随后又与创始人张兰爆发了激烈矛盾。
“你要对管理层的影响力足够大,但同时又能依靠他们做事情。” 一位资深 PE 投资人说。
孙强认为:“我觉得做 PE 的作用是协调各方利益、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协调 GP 与 LP 之间的利益、投资方跟创始人之间的利益,同时还要解决经营上的问题,财务上的问题,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企业越认可投资方。”
回看孙强经手过的那些成功项目,首先都是有一位优秀的创始人或管理团队,是股东之间配合默契,投资方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他催促亚信上市融资过冬;富力地产上市时,华平提高了认购额,成为基石投资者帮助其提振市场信心;投资银泰和红星美凯龙后,孙强帮这两家企业找到了 CFO、引进了管理组织的 EPR 系统,还帮助银泰招股上市。
他认为,媒体喜欢歌颂企业家的成功,以成败、以金钱论英雄,但他觉得,评价企业家,不能只看结果,还要看过程。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做事要经得起推敲,成功背后的每一步都可追溯,而不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其次才是财力、市值上的成功;最后还得看股东、员工、用户对你的评价。” 孙强说。
PE 的成败除了投资人的眼光与能力,还要取决于一个商业社会的成熟度——有没有一批好的企业、一批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以及一批足够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群体。“成熟的商业社会才有 PE 更多的机会。” 他说。
牌桌缩小,但 PE 仍有机会
2013 年,华平中国区的投资和退出的金额、产生的利润都创出新高。可能由于中国的业务在华平全球所占比重大大提高,纽约总部开始加强对中国运营的全面管控,此前十几年相当程度的自主权逐渐被削弱。
对此孙强不甚赞同,认为在政经环境瞬息多变的中国,本土化的战略和决策是成功的要素。如果把权力集中到万里之外的纽约,策略和执行的偏差会大大影响中国的业绩。“总部的话语权过强,团队容易失去参与感和满足感就没了,最后成就感也不会有。” 孙强说。
与全球 CEO 几天的长谈无果,孙强决定激流勇退,辞去华平亚太地区董事长的职务,把中国团队的管理权交给黎辉。2015 年中,孙强加入华平 20 年整之际,他正式离开华平,创办了从事农业投资的黑土地集团。
这次创业的跨度非常大:孙强和一位黑龙江当地的企业家合作,与北大荒集团签署了 100 万亩耕地的 50 年流转协议并入股北大荒薯业集团,立志把这家老牌国企改制为现代化经营的企业。同时,他们在黑龙江著名的水稻产地响水流转了 10 万亩良田,希望打造一家种植、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的有机大米企业。
事实上,孙强低估了土地流转、国企改造、粮食加工、品牌创建、产品销售这一系列的挑战。三年后,与黑土地合作的北大荒集团领导调任,响水种植基地所在的相关官员因经济问题被判刑,薯业集团经营艰难,土地流转未能实现。
孙强经过深度反思,决定忍痛止损,退出与北大荒的合资企业,收购水稻公司 100% 的股权,潜心打造健康、美味、安全的东北大米企业。经过他和团队的八年奋斗,今天的黑土地是一家提供从田间到餐桌的美味大米的全产业链粮食企业,实现了稳定盈利。
这种既能获得利润、又能带来社会价值的投资模式即所谓 “影响力投资”。它的涵义是通过投资支持创造社会价值而又兼顾财务回报的企业。这也涵盖 ESG 与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概念。孙强说,“我坚信它是投资界的未来发展方向。” 此后数年,他一直坚持这种 “影响力投资” 的模式,用自己的资金支持了多家在教育、减碳、光伏、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初创企业。
也是由于这方面的涉猎,2017 年,在影响力投资方面独辟蹊径的美国大型资管企业 TPG 吸引孙强加盟,全面掌管其中国区投资业务,包括它的 “Rise” 影响力基金的中国区投资。
TPG 计算影响力的方式是投资者将其被投企业取得的社会效益乘以其持股的百分比,算出最终投资份额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再经过严格的第三方审计后汇报给 LP 出资方。
在今天的地缘环境之下,“这是无论哪方政府都乐于见到的投资模式。” 孙强说。
然而,此时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在悄然改变。资本市场不再狂热追捧砸钱抢市场的企业,对于上市和并购企业的估值也回归理性。这意味着,VC 式高风险、高收益的爆发性机会大大减少——遍地是黄金的时代已经终结。
对 PE 而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孙强判断。未来的 PE 投资,将倾向并购控股型,而非以往简单的参股-上市-套利模式。
中国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已接近交接班时刻,但其中许多人没有二代接班,即便不顾及传承,创始人也开始考虑放弃家族治理的模式,走现代化企业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职业经理人群体越来越成熟,这为 PE 基金通过控股家族企业,提升治理水平与盈利水平,最终靠并购而非上市获利退出提供了基础。
“并购基金在未来会更加重要,至少在金额上会占很大份额。” 孙强说。PE 相比过去也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因为控股型交易相对复杂:投资人需要能够判断资产真实的基本面;其次要用金融杠杆和资本市场工具实现交易;第三要懂得如何控制和管理企业。
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今天的 PE 牌桌也在缩小。
过去两年,摩根士丹利亚洲基金没有在中国投出一个项目,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印度;像太盟(PAG)这样早就名声在外的大私募,因为它过往的投资多聚焦在中国,如今募集一支新基金也不如过去顺利。
有时候,孙强会怀念 PE 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蛮荒岁月,比如 2000 年前后,投资行业 “合作多,竞争少。”2003 年,孙强受邀出席了凯雷上海办公室的开幕;后来 IDG 资本在泰国举办了一个被投企业的 CEO 大会,同样邀请了孙强。
“现在?你想都别想了”。他说。
不过孙强对未来仍然抱有信心。他比这个行业里的多数人都经历过更多周期,“无论宏观环境有多难,还是会有很多好公司能从逆境中崛起。” 而对投资人来说,只要选对赛道,看准团队,把握好时机,就有可能成功。
“过去几十年,很多人把时代的赠予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未来要考验判断力、执行力这些硬功夫。” 孙强说。
题图来源:孙强提供
《晚点 LatePost》推出周末版,希望把视线扩展到各种各样的创造者。简单来说,我们想知道谁在创造,并以之影响周边;我们既注视当下,也回顾过去,寻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头;我们关注技术、商业,也关注历史、人文,打量这些领域的交汇处的涌现。
让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一款产品、一家店铺、一种包装的设计思路,也可能是某种工作哲学、产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种有趣新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焕发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相比有待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维克多·雨果的话——我们希望《晚点》周末印证这句话。
· FI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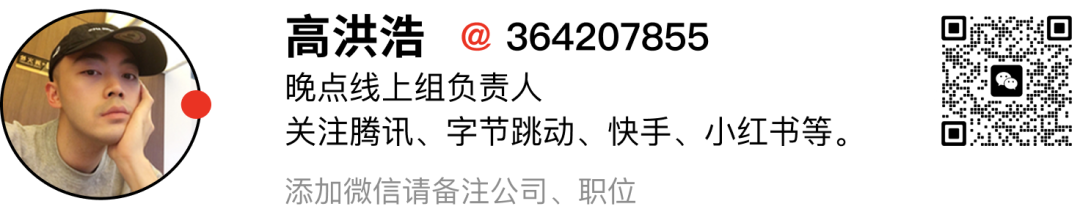

精彩评论